1950年,甘肃省金昌市的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在一个冰冷的冬日清晨,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地主被押赴刑场。当地大众纷纷议论,这位老地主多年来横行乡里,欺凌佃农,罪行累累。就在行刑前的最终时间,老地主忽然声嘶力竭地喊道:"等一等!我救过!"此言一出,在场的干部和大众都愣住了。这位甘肃乡间的老地主,怎么会和开国元帅扯上联络?并且还说救过他?合理人们将信将疑之际,老地主家人匆促赶来,手里握着一张现已泛黄的纸条。这张看似一般的纸条,终究藏着怎样的隐秘?它又将怎么改动这位老地主的命运?
1936年的西北,黄土高原上寒风凛冽。这一年的秋天,在甘肃会宁,赤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后,中心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络,从红四方面军中抽调了两万余名将士,组成了一支新的戎行——西路军。
西路军的建立可谓匆促,部队从长征中刚刚走出,许多兵士还未从疲乏中恢复过来。这支部队由担任总指挥,陈昌浩担任政委,他们肩负着开辟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重担。可是,摆在西路军面前的困难远比幻想中要严峻得多。
首战之地的是地势问题。河西走廊区域地势杂乱,既有连绵的山脉,又有广袤的戈壁。关于大多数来源于南边的赤军兵士来说,这儿的环境分外生疏。冬天的河西走廊,昼夜温差巨大,白日酷日当头,夜晚寒气逼人。许多兵士只要单薄的戎衣,底子没办法抵挡酷寒。
更大的要挟来自马家军。马家军是由马步芳、马鸿逵等人组成的当地武装,他们长时间占据在西北区域。这支部队不只配备精良,还得到的全力支持。马家军的兵士都是西北本地人,他们体格健壮,了解地势,还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。在作战时,他们常常使用本地地势优势,采纳游击战术,给西路军造成了巨大的困扰。
1936年11月,西路军在永昌邻近与马家军展开了剧烈的战役。马家军凭仗优势军力,采纳了围点打援的战术。他们先是堵截西路军的补给线,然后使用马队的机动性,对西路军施行切割围住。西路军尽管奋力反击,但在配备和补给都处于下风的状况下,战役反常困难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,西路军的后勤补给日益严峻。由于当地气候酷寒,农作物产值有限,加上马家军采纳了坚壁清野的战略,西路军常常堕入粮草匮乏的窘境。兵士们有时只能靠吃野菜、树皮来果腹,有些人因而患上了严峻的营养不良。
到了12月,西路军的境况愈加危殆。马家军在得到援军后,进一步加大了进攻力度。他们采纳涣散围住的战术,将西路军切割成数个部分,各个击破。西路军被逼转入防卫,但在敌众我寡的状况下,防地不断被打破。
1937年头,西路军的境况益发困难。继续的战役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,两万余人的部队已所剩无几。3月的一个清晨,马家军忽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,强烈的炮火将西路军的阵地炸得四分五裂。西路军被逼涣散包围,部队的建制被完全打乱。
带领仅存的一个保镳排,在刀光剑影中突出重围。这支缺乏三十人的小分队,带着着最终的通讯设备和重要文件,开端了困难的东进之路。为了避开马家军的追捕,他们只能挑选人迹罕至的荒漠道路。
这条道路穿越了甘肃境内最为荒芜的地带。白日,酷日当空,沙尘暴虐;夜晚,寒风刺骨,温度骤降。保镳排的兵士们带着仅有的几壶水,在苍茫戈壁中困难行进。他们不得不采纳昼伏夜行的方法行进,以逃避马家军的查找。
马家军对的追捕反常凶恶。他们派出了数支精锐马队队,在各个或许的道路上设下匿伏。一起,马家军还在沿途村庄张贴了赏格告示,许诺重金缉捕。这使得保镳排不敢容易挨近人迹密布的当地补给。
行军途中,兵士们的物资逐步耗尽。有的兵士因脱水而晕倒,有的因饥饿而无法继续行进。为生计,他们不得不吃野草根、喝露珠。带领着兵士们在荒漠中寻觅仙人掌,用刀割开汲取其间的水分。
3月中旬,当部队行至永昌近郊时,状况到了最危殆的时间。接连多天的行军使兵士们精疲力竭,带着的通讯设备也由于沙尘的腐蚀而产生毛病。更糟糕的是,他们的后路被马家军切断,前方则是一片不知道的荒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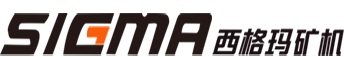



 在线咨询(7*24)
在线咨询(7*24) 电话咨询
电话咨询